《慶余年2》第15集中,御史賴名成下線,又一段很有力量的悲情高光戲份。
這大概是第9集范閑喚醒鄧子越之後,又一直擊人心的重鎚。
你看,若說戲份說番位,飾演賴名成的畢彥君,戲份很少、四捨五入恐怕連「男十八號」都未必算得上。
但這根本不重要,重要的是「賴名成被廷杖、而范閑監刑」、戲很動人。
來,展開說說。

一,將他理想碾作塵、再逼他和淚含血吞
都說諸多朝代是「儒表法里」,而慶帝連「儒表」那點皮面也不裝了,滿手血滿身威滿面「天威難測,聖心如淵」,玩的完全是「明」君無為於上、群臣竦懼乎下那一套;他當然不是真搞法制,而是權謀制衡:都跪好了、當戰戰兢兢彼此牽制的人形玩偶。
范閑終於在陳萍萍提示下接旨,跪下時應聲響起雷鳴,范閑悲肅的無聲和炸雷的轟鳴,炸起一段大悲血雨。

這一段里宮殿建築、乃至雨水雨傘,雖則無言、但也都是表達的有機部分、共同構成了喋血悲涼畫卷。
先說宮殿,君權牢籠的具象化、無聲巨獸的壓迫感。
范閑瘋狂跑向行刑處,平常上朝時熱熱鬧鬧的迴廊、如今寂寂杳杳,偌大一個宮殿、只餘三三兩兩小太監。陰雨綿綿、長空黯黯,巍峨宮殿的莊嚴、對比范閑的慌亂疾馳,像山嶽般沉默的巨獸,吞噬范閑的血肉。

范閑問「賴名成在何處廷杖」,雨中雕欄畫棟皆無言、深宮寂寂全無聲,唯有一隻鳥兒微微探頭。你看,飛檐畫閣森冷、像一層層牢籠,鎖大慶滿朝文武無人敢直言,鎖孤臣喋血、鎖少年白頭。
鎖他熱血從頭被澆冷,鎖他諍友笑談變死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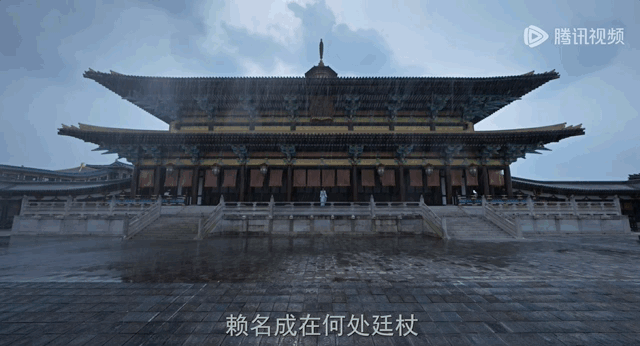
從疾馳飛奔慌亂找人,到廣場上孤零零一人的無助,再到宮門行刑處,這一段剪輯進的不同鏡頭,有對準慌亂腳步的特寫,也有固定機位遠景「空蕩蕩廣場上只他一人」,也有跟隨他背影略帶搖晃感的處理,能明顯看出跟著故事跟著情緒的有機絲滑。
范閑終於找到行刑處,窄窄一道宮門、高高四面屏障,四處滿溢著壓抑感。
風雨如晦、忠臣枉死。

再說傘。
傘是物理的實際的傘,也是心理的象徵的傘。
范閑希望是賴名成的傘,敬他孤直、尊他清正,喜他耿介、仰他磊落,表面上是參和被參、罵狗和被罵狗的關係,實際上是心無靈犀但大道相同的諍友。
賴名成表面上是個頗為迂腐的「傻讀書人」,實際上某個部分和范閑一樣,訴求是「絕對權力的去絕對化」,是「對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帝制皇權的監督」。

范閑推開侯公公遞來的傘,賴名成慘被廷杖、生死一線:我有什麼臉有什麼心情顧著打傘?
而賴名成死後范閑又撿起地下的傘、遮住賴名成遺體,此時是「除了為他撐一把傘還能做什麼」。

范閑走向賴名成,鏡頭是俯拍機位,人像一個小豎點一樣錯落煙雨中,而雨水有短劍有匕首一般的有形感,有一種「小小玩偶被無形之手操控」的碾壓式的縱深。
范閑為賴御史撐傘之後,鏡頭緩緩拉遠,蒼涼凄惻;此後的轉場,從行刑場景到馬車,是雷聲轟鳴和車軲轆聲轟隆的「同聲」聯結,也是范閑內心山崩地裂的情緒外化。
血肉模糊的何止是賴御史的肉身啊,那也是范閑被侮辱被損害的人間理想。
慶帝毀他錦繡清平夢,擊他至寸寸玉碎,將他千般理想萬般願景都碾作塵,再逼他和淚含血吞。

此前「家宴」上慶帝為范若若指婚,如今慶帝命他為賴御史監刑,君威壓四海,范閑一碎再碎一慟再慟。
長門長、深宮深,歲月寒、衣裳薄,范閑這條路、風霜刀劍嚴相逼、步步血淚時時殺機。
但正因如此才格外動人不是嗎?
一曲喋血長歌,淚盡了還啼血,正是因為一再被碾碎、才更堅定更九死不悔。

可憐可恨,那慶帝不問蒼生問神殿;
可悲可敬,那憂國憂民老臣心,以身殉理、以死相諫。
你看,范閑已經不是最初的范閑,他背著老金父女未完的樸素人生、未盡的血海深仇,背著賴御史未畢的清正諫言、未圓的理想大夢;
逝者已矣,當他們隨春風春雨再歸來,願范閑和夥伴們、已讓慶國人間更值得。

二,書房眾生相
賴御史一參再參再再參,這一段書房眾生相特別有意思。
辛其物是喜劇化的丑角,低階變色龍,上趕著拍馬屁總是拍不對地方。

林相、陳萍萍乃至戶部尚書范建,某種意義上都是能先一步明白帝王心的老(權)臣,只是他們「置身事內」的程度又很不同。
慶帝問如何處置,范建范閑父子力保賴老頭,只是兒子說賴御史有功,而父親更懂得將畫風轉向「陛下寬宏大量」。
秦業說降官,而林相說「賴名成罪無可恕,可是陛下仁德天下皆知」,給罪名定性「忤逆陛下」,強調陛下「仁」、更強調「全憑聖恩」「陛下聖裁」。
你看,只有范閑一個人真正講對錯。

林相也好陳萍萍也罷,都很早就明白慶帝殺心已起、而范閑不明白。
范閑不明白和辛其物抱大腿抱不對節奏不同,他不是看不破、而是依舊懷抱一種過於理想化的天真。
慶帝說「要賞」之時,范閑高高興興以為真要賞賴名成;賴名成的賞賜忽然就變成了死罪,范閑措手不及驚愕萬分,你看,他一度真心以為慶帝會更好世界會更好。

兩位皇子,從一路表情複雜看賴御史「殺瘋了」,到太子掐大腿嚎哭、和辛其同流合「丑」;都是野心家都瘋癲,但對諸多細節的態度都很不同。
賴御史每個階段拋出不同的雷,一眾人等或早或晚或悲或驚的反應,已知未知的時間節點等等,都很有看頭。
從某種程度上說,這段戲好在「從任何一位的視角,都可以交錯縱橫又嚴絲合縫重新理一遍故事」,信息量極高,但不碎不枯燥。
這麼多人的群像,這麼複雜的大戲,從喜劇諧謔小丑登場、到眾人當堂打御史的荒唐,再到真正的喋血悲涼,劇作調度和把控能力很好。

賴御史背後,站著歷朝歷代諸多清正身影。
一包紅棗清貧而來、兩袖清風翩然而去,青史留名一點丹心、宮門喋血一片忠魂。
賴御史此前參范閑、然後參陳萍萍,都是御史之職(御史監察百官,明代改御史台為督察院);賴御史御前殺瘋了,參完監察院又參慶帝,這一條其實更接近「諫諍機構」官員的工作。

「諫諍機構最主要的官員,先後有諫議大夫、拾遺、補闕、正言、司諫、給事中。其職責和御史監察鋒芒指向百官不同,而是向君主進諫。」「君主專制制度下無真正法制可言,御史、諫官兼職者並不罕見」(引自祝總斌《君臣之際:中國古代的政權與學術》)。
《慶余年》是一個架空故事,劇中監察院明面上更接近「帝王耳目之官」,督察院(御史台)一度淪為閑置,而諫諍機構目前在劇中尚未濃墨重彩出現(還是那句話,監察院目前明面上接近慶帝耳目)。
范閑要做的不僅僅是diss慶帝或者嘎了老登,而是確保一種制度性的權力制衡。
不是個人權謀野心的「讓底下人互相制衡」的權術,而是另一種更文明更法制更理想的未來。

《慶余年》往前進的一大步,就在於范閑也好賴名成也罷,都不說「清君側」、不說奸臣蒙蔽君主。
不是那種「浮雲蔽白日」「讒言遮聖心」的模式,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指向慶帝這個老登且越過慶帝,從點到面更有普世性。
范閑質問「萬民和陛下到底哪個重要」,早就有標準答案:民為貴君為輕;蒙蔽住慶帝的不是次元壁,而是他自己的慾望。
封建君主製為何腐朽,《慶余年2》在用血肉真心用一個個「鮮活又慘死」的悲劇,回答這個問題;不是乾枯教條,而是入骨錐心之悲,是摧枯拉朽之力量。
老金頭殞命長街上、金家女香消凄風裡,賴御史喋血冷雨下、小范閑含恨宮牆內,而雨總會停、天總會亮。